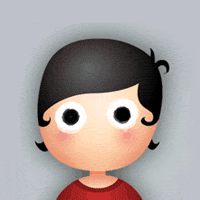前言
如果说能有一个更好的遇见的期许,为什么不?如果说现下的再见能换来一个还算可以的期许在前面的路上的牵引,我觉得我会愿意。
因为,这不是任何妥协,也不是任何放弃。
当我们不再是青年,当我们在日渐日的增加着遗憾着一些东西,比如再无能为力的往逝,或是怎么也无法实现的理想,那么起码在可用功的现在做点什么。
亦如今日的新知,来自蔡康永,我们其实要珍视人体的一些负面情绪。他列举道,悲伤促使我们深刻思考,愤怒使我们转变思维,遗憾使我们追求更好的自己。
这些情绪或许都是大部分人在正常境况下主动选择去规避的,但事实是,如若没了这些情绪,我们的人生将会变成纯净的傻子的狂欢。而那样的皆大欢喜对于我们终将面临的那次最重大的告别——死亡,只会是连杂质都是惨淡味道的白水,届时将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一具躯体也曾经呼吸过。所以,哪怕暂时的再见不尽我意,但我的这一作为所带来的思想拉扯至少让我留下了足迹。
今天的文章来自反骨的阿新,是一位我在大学时候便因偶然看了他一篇文章而忠实起来的作者。反骨与陈一格,大约存在一个共性。从未提及陈一格的来历,今天也顺势一提,一格,ego,是想告诉自己要做天生的自己,也许会显得自我,但那就是该有的模样。
很开心很荣幸能读到一篇激起内心深井涟漪的文章,特意请了授权,也分享给在看着陈一格的你。
再见啦,写诗的少年
原创 反骨 2018-05-16
作者 阿新
有些世故,有些人情,会让你想起另一个自己
回头看到破碎,向前望见徒劳
如此迂回一生
“我远远望见隧道尽头的光,而他孤独的站在光里,满眼忧伤的向我求救。我终于意识到,这是他最后一次醒来了,所以才决定像个绝望而勇敢的者,在一条穿越清醒与梦境的隧道,与我打个照面,礼貌告别。”
正 文
他想起那些书写在小镇废墟的诗。少年人奔跑过晨光与暮霭,在如织的细雨里,写下一行行让自己心动一生的句子。那时他怎知,自己将会耗尽漫漫余生,向那个斜风细雨的长夜告别。
后来的他每向前迈出一步,灵魂就被套上一重枷锁。
世人都说,人要往前看,他却常在无眠的深夜回头。他睁着眼做梦,梦见自己拨开废墟的荒草,看着那些诗句片片驳落,一笔一画,乘着晚风飘走。他忧伤的向四周呼救,可沉寂的废墟里只有呼救的回响。
“再没有人会踏入这土地了。”他说着,闭上眼沉沉睡去。
他沉睡时,我便苏醒。
斜阳透过窗台的空酒瓶,落在另一堆空酒瓶上;指尖掉落的烟灰,落在昨天掉落的烟灰上,我对着镜子摸了摸隆起的腮帮,举起头把水送往喉咙,埋下头看见满池殷红,火大,智齿疼的厉害。
一路摇摆着闯入闹市,再抬眼,阳光就不再柔情。我又要穿过人潮和水泥丛林,奔赴那些无意义的社交场了。
在巨大的会议桌前,在赶往片场的剧务车里,在街角的居酒屋中,在味同嚼蜡的德国餐厅,我怀着一颗沉默的心,开始无休止的说话。商务提案开始的时刻,摄影机移动的时刻,酒杯碰撞在一起的时刻,我认识了多少新的面孔,就遗忘了多少旧的身影。
世人都说,人要往前看,我二十六岁了,听得懂,也看得见,所以告诫自己别回头。
辛勤工作、宽厚待人、相夫教子,你我被这些看似友善的字眼裹挟着前行,不知终点何方,更不知去往终点的意义。不再一意孤行的我们,如那陡山上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,把巨石推上山顶,再看着巨石坠落山崖,如此迂回了一生。
“这是老一代叛逆者、摇滚客、愤青、激进分子、文痞、画痞变为善良父亲的时刻,是他们砍杀一生,佛前滚鞍下马的时刻。”
陈丹青的忧伤,让他把那个时刻描绘的更生猛,也更无力。而当盲目前行的我们,看到彼此脸上的不安和沮丧,也就目睹着他口中“佛前滚鞍下马的时刻”,在每一张更加年轻的面孔上,加速降临。
那个时刻把年华拉开一条长长的裂缝,我在那条裂缝里睡去,他在那条裂缝中醒来。
他又想起那些十五岁就学会穿高跟鞋的姑娘。少年人聚集深夜大排档,就着深冬的月光,喝下煮沸的啤酒,糯米粒留在嘴唇上,她不怀好意的伸出舌尖,隔着淡淡烟雾一脸坏笑。
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十五岁少女的爱情,也没有人能抵挡一个十五岁少女不怀好意的笑。
后来他见过的每一种风情,都被融化在那个转瞬即逝的微笑里。
他如是追忆着,又陷入那清醒梦境。他梦见一双红色高跟鞋在楼梯上踏出旋律,他们沉默着登上小镇最高的天台。对视、微笑、落泪、褒奖、侮辱、深情、仇恨,年轻的他们在高空撕扯,努力把想象中爱情应当经历的一切情绪、应当体会的万般滋味,统统释放在那个晚风荡漾的深夜里;年轻的它们心知肚明,哪怕有人错过一个呼吸,都会有另一个坠入万丈深渊的灵魂;年轻的他们玩够了,精疲力竭,终于被黎明的第一束阳光击碎,淹没在小镇无数忧伤的故事里。
“那是我最无知和卑微的时刻,也是我最偏执和勇敢的时刻。”他念念有词,再一次沉沉睡去。
我再一次醒来时,身处一场推杯换盏的酒局。男人的酒瓶与烟灰,姑娘的脂粉与眼泪,在暧昧的霓虹灯下,在嘈杂的摇滚乐中,洒落到天鹅绒织就的地毯上。时而有人凑向我耳边私语,醉到酩酊的我一句也听不进;时而有人向我递来香烟,我向四周张望,找不到打火机的身影;时而有路人向我招手致意,我记得他们的容颜,却想不起何时有了交集。声色犬马的场合,“在场”显得意义非凡,它象征着我没有在挥霍青春的盛宴里缺席,象征着我没有与那些向往自由的灵魂脱离。
清醒时我总是担心,担心我很早就老去,连微笑都会皱纹。
我再一次醒来时,坐在一场盛大婚礼的宴席角落。交响乐奏鸣,新娘一袭白纱,挽起儒雅的父亲穿过鲜花拱门,款款走来;长廊尽头的新郎数着妻子迈出的脚步,满眼深情。历经多少拉扯,才让这条长廊足以脚步丈量,他们最清楚不过,在场那些曾经蠢蠢欲动、如今安分守己的见证者,也最清楚不过。我看见他们的眼眸中泛起泪光,为这巨大的仪式感所洗礼,为他们逝去的年华所默哀。
几乎就在那一瞬间,我决定向远方出逃,哪怕逃不掉,我也不想要这囚禁灵魂的热闹。
我再一次醒来时,躲在十字路口的树荫下抽烟。一口冰拿铁,一口软玉溪,一场夏日午后光明正大的街头偷窥,这是一个抛弃高级趣味的理想主义者,一个被烟火气喂养大的小镇流氓,观察世界的重要角度。我看见信手拈来的扒手,看见被驱赶的街头艺人;我看见孩子们无知无畏,看见老人和老狗举步维艰;我看见优雅端庄的城市白领,看见在网约车里匆忙补妆的陪酒妹;我看见与野狗抢食的流浪汉,
我看见混乱,看见谎言,看见悲欢。当我孤独伫立的时候,当我与真实世界抽离的片刻,这些巨大而虚空的词汇,都显得无比贴切。
我再一次醒来时,穿过了一条长长的隧道,穿过了自己。
我远远望见隧道尽头的光,而他孤独的站在光里,满眼忧伤的向我求救。
我终于意识到,这是他最后一次醒来了,所以才决定像个绝望而勇敢的者,在一条穿越清醒与梦境的隧道,与我打个照面,礼貌告别。我常想,我们一定在自己生命的时间轴上有过片刻的重合,所以仍有些关于他的模糊轮廓,残存在我破碎的记忆里。
所以这是我们重逢的一刻,也是我们告别的一刻。
逆光之中,疾驰的汽车穿越隧道,碾压过他枯瘦的身影。我告诫过自己别回头,所以听到身后梦破碎的声音。
再见啦,写诗的少年。
Wechat:TheAntibone
全世界都睡了,就你一个还醒着
▼
2018-05-16 21:33
前言略长,但我这次不嫌自己啰嗦。
今日也宜晚安,晚安。
ALWAYS NIAN CHEN